廖鴻基,臺灣文學作家,曾從事漁撈工作。三十多年來將海上經歷化作筆下的文字,將人們與大海的關係娓娓道來。從一名年輕的漁夫,到鯨豚觀察者,再到海洋文化的傳承者。透過他的筆觸,我們得以窺見廣闊而神秘的海洋世界,感受台灣海洋精神的深刻詮釋,並重新思考我們與這片湛藍海洋的深層連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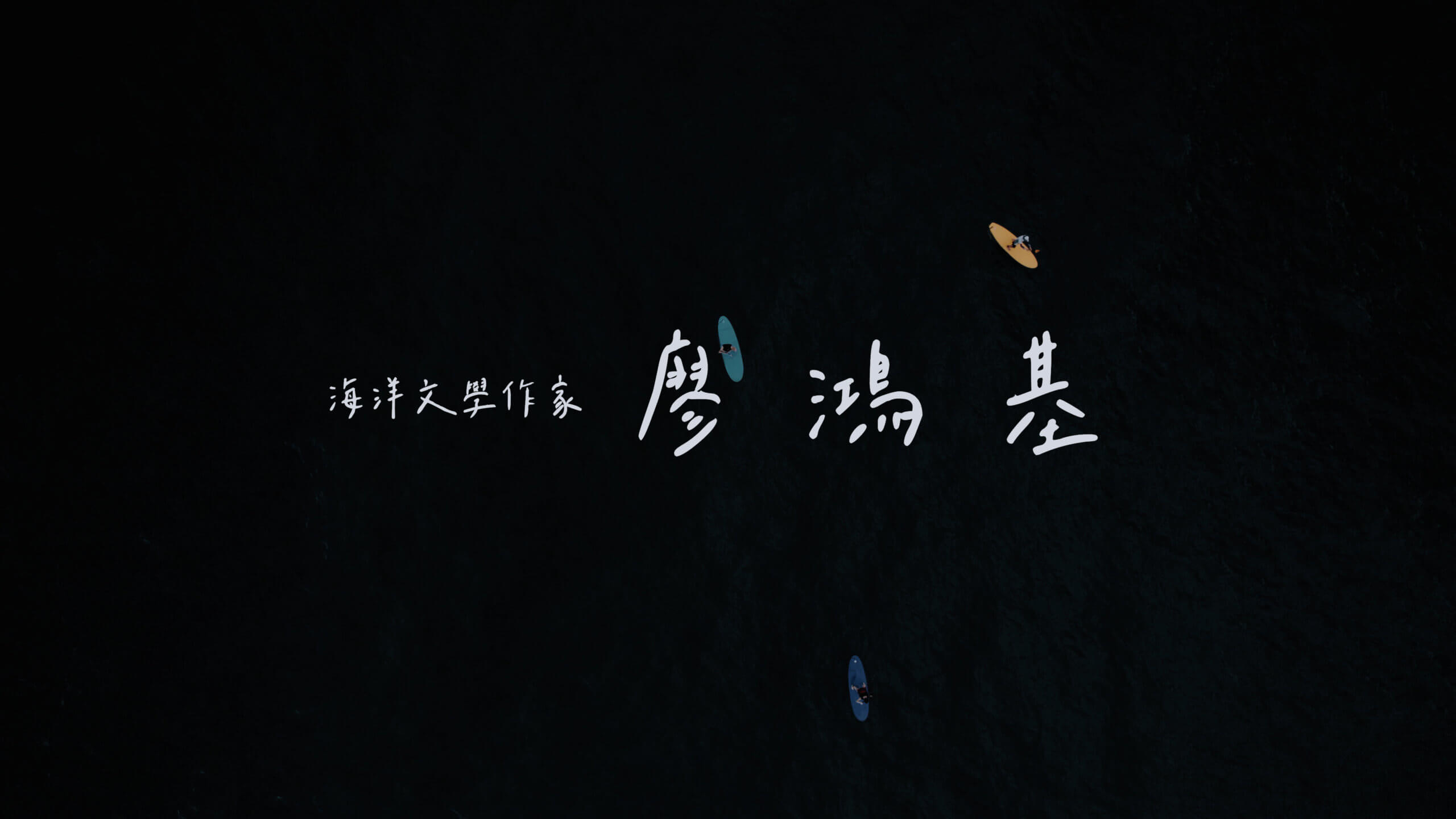
Good Life(以下簡稱為GL):請老師您先自我介紹。
我是海洋文學作家,大約30歲時,選擇到海上,在海上生活已經有30年了。
曾經做過討海人,也參與過鯨豚觀察,還有現在的賞鯨活動。一路走來,將海上的生活經驗和感想寫成了文學作品,最終成為了一名海洋文學作家。

GL:從您第一本書出版到現在,已經過了三十多年。如果再加上您參與的集體創作,總共大約有三十多本作品了。老師一開始是因為對海洋感興趣才接觸海洋,還是因為成為了討海人,才逐漸對海洋產生興趣呢?
我在花蓮長大,花蓮靠海面積不大,一邊是山,一邊是海,因此從小許多活動都與海相關,比如中秋節去海邊賞月,青少年時期情緒不穩定時會去看海,第一次約會也在海邊。海邊成為我們經常活動的場所,從小就陪伴著我。
因此,看著海天交界線,我心中常有憧憬,期待有一天能到那裡去。航海也成為東部人常有的嚮往。30歲左右,因為在陸地上生活困頓,我開始想,海洋這片空間或許能夠提供我疏解的機會。於是,我決定到海上去。
當時是戒嚴時期,上海並不容易。最簡單的方式是成為討海人,辦一個船員證,找一艘願意收留你的船,成為海咖。於是,我在30歲左右,成為了一名討海人,開始了海上生活。

GL:是什麼樣契機讓您想要開始寫作,或者記錄自己的感受呢?
海上的生活實際上是重勞力的漁撈工作。我發現,海上與陸地是完全不同的世界。到海上後,幾乎所有事情都需要重新學習,如何吃飯、如何在甲板上睡覺等。海上的一切,無論是視覺還是感覺,都非常新鮮,這些新鮮事物總讓我想與人分享。例如,回到陸地時,我會告訴朋友今天在海上遇到了多大的雨,或看到了什麼風景。
但由於我過去有語言障礙,不太喜歡用口語表達,較習慣用文字來表達,因此最終選擇用文字來描述我對海洋的感受。對我來說,文字比口語更為舒適,是我習慣的表達方式。

GL:您是先成為討海人,才開始寫作的,剛開始寫第一本或第二本書的時候,一定會遇到一些困難,比如覺得自己有沒有寫到位,或者在書寫過程中遇到的挑戰。能否分享一下這些經歷呢?
當然會有困難。畢竟我沒有接受過文學訓練,學生時代也非常討厭寫作文。因此,我既不知道文學是什麼,甚至不清楚散文或小說的架構。在這樣的狀況下開始寫作,當然會遇到挑戰。
最大的難題是,我過去並不是一個愛閱讀的人,讀過的文學書籍不多。於是,我選擇了另一種“閱讀”方式
讓我的腳步帶著身體和感官進入海洋這片文學世界,充分“閱讀”海洋。
我的書寫往往都是親臨現場,必須感受到或被感動,才會去進行表達。
但閱讀量確實也成為我寫作上的瓶頸。每一位藝文工作者都需要不斷突圍、突破,簡單來說就是要超越自己。只有藝文能力提升,表達才能達到相應的高度。
開始寫作後,便開始努力在這方面提升,多讀書、多觀察世界,了解文學和藝文的真正含義。

GL:比較像是一種紀實的方式,去記錄下自己所感受到的感動。
當時,由於海上工作比較忙碌,寫作便從最簡單的短文開始寫起,也是後來才知道,哦!原來這就叫散文(笑),散文本來就是即時性的書寫。
開始寫作後,變有一股強烈的衝動,因為我其實比較喜歡小說。在後來的閱讀中,我更偏愛小說,因此心中有完成小說的願望。
當海上活動減少,時間變得充裕時,我便開始嘗試小說的書寫。

GL:能否與觀眾們分享幾本小說呢?
過去我參加散文文學獎時,評審常給我「我的散文很像小說」的評語,我也發現自己其實喜歡用小說方式講故事。
最近幾年,我出版了幾本書,包括短篇和長篇小說。短篇小說《魚夢魚:阿料的魚故事》以超現實主義講述魚的故事。
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《最後的海上獵人》講述了鏢旗魚的故事。我曾參與鏢旗魚的漁撈活動,認為這是台灣精彩的傳統文化,目前也僅剩台灣保留這種傳統。
這種文化需要長年積累才能形成,我認為有責任將它寫下來,因為它正逐漸消失。大約五、六年,頂多十年,它就會完全消失在我們眼前。所以,我認為我應該將這麼精彩的海上魚撈作業記錄下來。

GL:老師您講的消失是指旗魚這個物種,亦是這項捕撈方式呢?
兩方面都有。首先,因為這種方式與現代科技相比,捕獲效率不高,現代技術如「定置網」和「流刺網」都能夠捕獲更多魚類,因此這種捕撈方式注定會消失。
其次,雖然這些魚類是可再生資源,但過度捕撈會導致數量減少。白肉旗魚也因為過度捕撈,數量已經在逐漸遞減。在這些條件下,它們都注定會消失。

GL:老師您的作品蠻多是描述魚類跟人類之間的互動,蠻多靈感是您出海的真實故事,那這三十幾年的海上生活中有沒有比較難忘的經歷呢?
在從事海洋工作之前,我對海洋世界充滿嚮往,因此經常沿著海邊走,後來,也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多次走完花蓮到台東的海岸線,並在過程中寫了一些關於海岸的文章。
30歲後,我開始從事海洋漁業書寫,並進行了鯨豚觀察,記錄了海上生活的點滴。雖然這30年來我一直在同一片海域,但由於從事的活動不同,留下的記錄也各不相同。
台灣的海洋生物資源非常豐富。例如,全球魚類中台灣約能見到四分之一;海龜可見七分之五;鯨豚類能見到三分之一。因此,台灣的海洋生物資源是非常豐富的。
老船長一輩子都在海上捕魚,有時候捕到一條魚,我問他這是什麼魚,他也答不出來。捕了一輩子,竟然還會捕到從未見過的魚。
在出海的日子裡,我經常遇到超出認知的新鮮事物,幾乎每天都創下新的記錄,見到一輩子未曾見過的全新物種,海洋的神秘與豐富確實讓人驚訝。
常常有人會問我,寫了三、四十本海洋文學,是否還有題材可寫?
即使一輩子多麼認真努力地航行,也無法遍及大海的每個角落。因此,海洋是一輩子也無法寫完的題材,因為它既寬廣又深邃。

GL:除了寫作,您也有推很多跟海洋相關計劃,例如:抹香鯨計劃、黑潮漂流計劃等,怎麼會想要發起這些計劃呢?想傳達的理念為?
我們一輩子就像爬樓梯,每爬上一層樓,就會有新的視野。海洋也是如此。
當我在海上捕魚,遇到鯨豚時,發現我們的海域如此豐富,卻鮮少被社會所知。於是,我組成了尋鯨小組,開始進行鯨豚觀察和相關活動。
現在,我們在進行太平洋抹香鯨計劃。2018年,我們發現台灣東部的太平洋中有抹香鯨。抹香鯨成年可長到18公尺,也是目前為止發現的兩種大型鯨類之一。

這項計劃對外是希望台灣因為抹香鯨,引起國際關注,讓世界看到台灣;對內希望台灣社會知道我們不僅有台灣黑熊,還有神秘的抹香鯨,也因為抹香鯨轉過頭來,看見我們的海,珍視我們的海。每個計劃大概都是開創性的,過去沒有人做過。
我常覺得這是應該做的事情,並且需要認真努力做好。比如黑潮漂流計劃。黑潮大概是屬於地球等級的主環流,它的流速和流量都相當驚人。如果台灣能夠利用黑潮帶來的生物和非生物資源,大概會讓台灣的體質有所改變。然而,我們對於黑潮的了解仍然有限,因此才會開展這個計劃。我雖然不是海洋學者專家,但我相信只要去搭乘黑潮、閱讀黑潮,都可以讓台灣社會注意到這麼大的天然力量就在我們身邊。
繞島計劃也是如此。台灣是一個島,為什麼很少有人執行繞島旅行?熱愛海上活動的青年,應該都有開著船環島的夢想。因此,我在2003年發起了繞島計劃。當然,這些都是創意和發起的角色,希望能激勵更多年輕人追尋海洋夢想,完成更多海洋相關的計劃。

GL:您有創辦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以及花蓮福爾摩沙協會,那這兩個組織代表的角色是什麼?為什麼會想要籌備這樣的單位呢?
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於1998年創立。這是因為1996年我進行了花蓮海上鯨豚觀察,並在1997年推行了賞鯨活動,希望改變台灣社會對海洋的看法。然而,單靠一人的努力不夠,如果能有一群人一起做的話,應該很快就能達成目標。因此在1998年我創立了黑潮海洋基金會,借助更大的社會資源來推進這一目標。
花蓮縣福爾摩沙協會成立於2022年,起因於我們在太平洋發現了抹香鯨,並認為這是改變台灣的契機。擁有抹香鯨對內、對外意義都非常重大。然而,詢問過黑潮基金會後,發現他們的業務已經飽和,無法接手這個計劃。因此,我們從零開始,成立了花蓮縣福爾摩沙協會,執行這一項夢想計劃。每個團體都有其自己的角色和業務。

GL:您會如何看待現在社會的海洋的保護意識呢?
首先,海洋是地球生態的母體,也是我們的最後防線。過去,台灣社會缺乏海洋教育,加上長期政治戒嚴,導致台灣人對海洋的親近感不足,對海洋的重視也不夠。
許多人仍然對海洋保持距離,甚至對海洋活動持保守態度,擔心接觸海洋會有害。然而,我認為人類是透過學習而成長的。當我們擁有海洋意識,並將海洋視為自然的生活領域,透過接觸促使我們觀察並喜愛它,只要對海洋感興趣,我們就會關心它的健康狀態。
這是台灣社會需要的基本態度。上天賜予我們如此寬廣且資源豐富的海洋,以彌補海島的有限。若我們一直待在陸地上或背對海洋,對海洋是非常不利的。
我們已經把海洋的生物資源損害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,過去我們把鯨豚當作普通的魚貨,獵殺牠、享用牠們的肉,對它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,但當我們航向海洋,開始把它/牠們視為朋友時,就符合珍·古德博士的主張—只有接觸才能真正認識,認識才能達到真正的關懷。
不可能連接觸都沒有就關懷它/牠,我想那只會是一個形式上搖旗吶喊跟呼口號的環保意識。
我們需要轉過身,看見海洋、接觸海洋,對其產生興趣,才能真正知道如何珍惜它。
我比較不喜歡用「保護」這個詞,因為人類真的沒有能力去保護海洋這樣的母體。我們應該珍視它,減少對它的破壞,讓它能夠永續地提供我們所需。

GL:您認為台灣在海洋的保護這塊,可以學習或借鏡哪個國家呢?
我想應該有很多例子,許多先進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已經在沿海設置生態保護區。設立初期,當地居民往往會反對,因為這限制了他們的採捕資源,影響生計。然而,從長期來看,這些保護區使生態資源和魚類數量大幅增加,並且促進了觀光業的發展。許多人到這些海域潛水、觀魚或參與其他海洋活動,當地居民的收入也因此提高,這是一個成功的例子。
台灣也迫切需要推動沿海生態保護區,因為不做,可能會來不及,雖然這過程中可能會面臨漁業工作者的反對,但只要我們堅持,並參考國外成功的經驗,我相信這是可行的道路。

GL:有認識互動才會有關懷,那您會給予同樣喜歡海洋,並想瞭解海洋環境議題的觀眾什麼樣的建議呢?
接觸是連結的橋梁。當我們開始接觸海洋,便是好的開始,至少你已經願意靠近海洋。我建議年輕朋友們,若只是進行一次海洋活動,那可能僅僅是放鬆身心的娛樂。如果願意,可以為自己準備一本海洋筆記,記錄下每次活動的感受和過程。這不僅能讓海洋內化於生命中,也能在書寫中回味並深入思考,探索如何與海洋建立更健康的關係。
這樣的記錄不僅是個人的海洋經驗,未來也可能成為台灣社會與海洋之間更多連結的基礎。從這一步提升對海洋的興趣與感知,對台灣來說是非常重要的。

GL:您對於自己的創作,以及海洋的議題,有什麼樣的期許或是期望呢?
海洋的接觸是一步步累積的,就像逐浪而行。每踏出一步,便能看見下一步。經過30年的海上生活,我深知,海洋既無法走遍,也無法寫盡。
我記得剛開始在海上生活和工作時,台灣社會,甚至我的家庭都認為這不正常。當時我給自己設立了一個階段目標:寫完一本書後就回到陸地。然而,完成一本書後,我對海洋的興趣更深,投入更多。後來,我設定了三本、五本、十本,直到二十本的目標。達成後,我便告訴自己
活多久寫多久,海上生活也是一樣的。只要能夠出海,我會維持一輩子與海直接接觸的關係。

GL:最後,您個人對於好好生活的定義?
老天賦予我們每個人一種特質。像我喜歡文學,有些人則喜歡攝影。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,儘早找到老天希望我們完成的事,當我們找到那個位置時,即使工作再辛苦,也會感到愉快。
我認為找到自己的位置,便是好好生活的起點。

